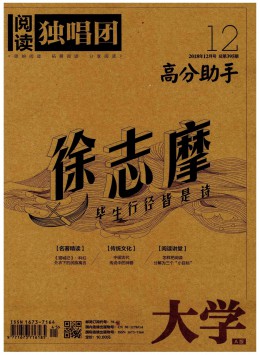大學教育目的存在之問題探討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大學教育目的存在之問題探討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大學作為培養人才的主要陣地,是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基地,是民族國家的文化、精神的象征。當今,大學教育以就業為指揮棒,功利性和工具性逐漸取代其價值性和理想性追求。大學教育應以學生的興趣為起點,以對學問的渴欲為最高目標,平衡通識教育和專才教育的關系,加強文化教育,為社會培養“不惑、不憂、不懼”的“整全的人”。
[關鍵詞]大學教育目的;整全的人;通識教育;專業化
當今世界,由教育所支撐的科學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競爭力的核心。眾所周知,美國崛起并稱霸于世界得益于二戰后的“人才戰爭”以及隨后的“人才引進戰略”,美國這種不問種族、不分國籍的“唯才是用”的人才計劃,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最多的頂尖人才。英國BBC援引OECD報告甚至聲稱,全世界62%的“頂尖科學家”都居住在美國[1]。由此可見,唯有人才才是國家真正強大的必須,唯有教育才是國家發展與民族興盛之關鍵。美國教育家科爾在其著作《大學的功用》中指出,大學是知識產業,是一個社會的核心,是實現國家目標的重要工具[2]。大學作為培養人才的主要陣地,是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基地,是文化、精神的堡壘。那么,何種大學教育能夠順應時代變遷培養出優秀人才?我們的大學應該秉持怎樣的教育目的,這是值得我們深思和探究的重要問題。大學教育目的,從廣義上講,是指在一定地區、一定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下,社會對大學教育的要求,是教育工作的出發點和最終目標,也是確定教育內容和評價教育效果的根據。從狹義上講,是指大學基于自己的性質和宗旨所設定的目的,體現了該大學的精神和特點,具有獨特性和差異性。狹義的大學教育目的,是大學教育實踐中追求的目標,故而被認為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教育目的。目前,我國大學教育似乎正在走向“歧途”,現實中的大學教育目的與《大學》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的“格物窮理”,梁啟超的“學做人”,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相去甚遠;與英國紐曼的“大學是一切知識和科學、事實和原理、探索和發現、實驗和思索的高級保護力量”[3],與德國洪堡的“大學是進行科學探索和學生個性與道德修養的地方”[4],與懷特海的“大學的任務在于把一個孩子的知識轉變為一個成人的力量”[5],相去甚遠。大學教育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我們不妨從以下三方面一觀。
一、“教育為考試,學習為就業”
林語堂先生幾十年前就發現教育制度存在的問題,他在《論學問與知趣》一文中指出,現行的教育制度,其目標、方法、制度,可以一言以蔽之:“教育為考試,考試為升學。”[6]107時至今日,我們不幸地看到,“以考試為中心,以就業為指揮棒”的大學教育制度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使得教育目標始終與啟發心智、培養人才之旨趣相去甚遠。“心愛,學問及人生———這是教育的正當行業……學就是喜愛。學生應該對這喜愛某種學問之發現,發出狂喜。”[6]107但是,現在的教育往往扼殺學生求知的欲望和自覺性,使學習變得枯燥,變得功利,變得被動,毫無樂趣而言。美國教育學家杜威犀利地指出:現代教育,如農夫養鴨到市去賣。強喂粟,粟愈多,稱愈重而愈好賺錢。丘吉爾說過,教育最重要的事是對知識的渴欲。教育非始于大學,也不應該終于大學。“學問為求知,求知在養趣”[6]107,教育的目的應在培育運用頭腦的能力,和以學為樂、為趣的境界。大學教育應該幫助學生養出“自我的生活”“自我的感覺”“叫人對于任何所行所作的事,養出可以終身行之的一種‘風度’”[6]108。顯而易見,好的教育應該將激發學生對學問的興趣及求知欲設為最高目標,一切教育手段以此為出發點和終點。然而,可悲的是,目前的大學教育是急功近利的,無論教師還是學生在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一切目標的驅使下,將知識的傳授和學習過程視為機械化生產,老師是熟練的技術工,將知識打包送上生產線,經過一模一樣的流程,最終制造出幾乎一模一樣的產品———學生。在整個過程中,學生是被動的,是無為的,是毫無個性和創造性而言的。更為可怕的是,學生在入大學選擇專業時,便是功利性極強的,什么專業薪資待遇高,什么專業社會地位高,什么專業學得輕松,什么專業就業前景好,這些成為高考生報考專業的決定性因素,而完全將個人的喜好、興趣置之一邊。據調查,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因素選擇大學專業的不足四成,而有六成學生對所選專業并不了解。“以擇業為目的”的選擇專業和學習成了大學極為普遍的現象。杜威早就指出這樣做的弊端:“預先設定一個將來的職業教育,損害現在發展的可能性。”我們當前的大學教育不僅不能使學生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得到延伸擴散,反而使其縮小和變窄。“學問起于好尚,而終于驚奇”[6]108,讓興趣和心愛成為大學教育的起點,才是大學教育應該變革的第一步。
二、“課堂有教育,學校無教育”
當前大學教育存在的另一大問題是“課堂有教育,學校無教育”。在大學中,學生一心為自己將來的出路做打算,因此,教師教的是知識和技能,學生也只學知識和技能,師生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日見生疏。師與道,顯然地劃開,成為有師而無道。換言之,是只剩了教育方法,而沒有教育精神[7]287。于是便出現了我們現在看到的,課堂上是師生,課下便成了陌生人的冷漠、尷尬的師生關系;出現了大學教師的“言傳”多于“身教”,且言傳也僅限于一些專業知識的傳授,并不涉及對于人生更為重要的人格、德性、理想等的教育和中國思想精髓的傳播與普及的現象。此等教育將教育的目標縮至一個狹小的閾限,使教育偏離了其最基本最重要的目的,完全受制于這些死板的、生硬的、不合理的課本和大綱。首先,大學教育之可貴者在于“大學環境內部實際生活之陶冶,而課業之研修與講堂之傳習為之次。”[7]194因此,大學教育者應該是一個“通才”,除專業知識技能外,還應在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方面有所涉獵,更重要的是,始終保持學習和探究的熱情。“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假使大學里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教育后進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成良好的學風,不斷培植出博學敦行的學者。”[8]其次,教師應在課堂教學上下功夫,應力求閎通,使學生擁有自由思考的空間和條件,使學生的思維猶如雛鷹翱翔,猶如池魚游弋,自在而無拘束。不僅思維可以如此,溝通亦然。就目前大學課堂現狀來看,學生充當著聆聽者,課中罕有主動與教師、同學的溝通交流,或辯駁觀點。學生們課上保持緘默的原因,一則并未主動思考,故無觀點可言;二則不敢、不愿直抒己見,唯恐遭人取笑,成為話柄;三則,缺失思維的批判性,人云亦云,對問題沒有獨特深刻見解。這樣一來,不僅會直接影響到他們接受知識的效果,更會磨滅了他們表達意愿和思維創新的能力,成為一個知識的“容器”,而非知識的使用者和創造者。教師應積極鼓勵學生在課堂上敢于、樂于大膽表達,提出觀點,哪怕是幼稚的,是不切實際的,甚至是錯誤的,我們應為學生創造這種不受限、無障礙溝通的氛圍。最后,學生在大學期間所遇到的困擾絕不僅限于知識方面的,在對人生開始思考的年齡,大學生更多的關注人際關系、自我坐標的確立以及擇業、交友等方面,他們的茫然和困惑體現在實際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大學教育目的如若僅局限于專業知識的傳授遠遠不能滿足學生作為一個人的成長的需要。有效的教育應放眼于學生之全面成長,思想之成熟,見識之廣博,心智之健全,人格之陶冶,個性之自由,使學生開拓情趣,暢悅胸襟,只有這樣,學生未來的生活才不會漫無目的,學業才不會偏狹機械,不會喪失群居之德和生活之樂。大學教育要實現如上教育目的最重要的要素是教授人才的充實,教育貴在“行不言之教”,為師者,需“能學究天人,通天人之際,守先待后,把此道來永遠傳遞給后代人”[7]283。為師者,旨在教人如何好好地做一人。只須樸實地,以身作則。梁啟超先生在《為學與做人》一文中也指出,進學校“為的是學做人”,為的是做一個“不惑、不憂、不懼”的人[9]。他建議我們教育者首先就應以這三件事教育自己。教師注重自身的修養心性,德性塑造,用自我的言行對學生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教化學生,這才是“學高為師,身正為范”。同時,教師還應以自身的經驗和學識高瞻遠矚地為學生的未來發展提供有針對性的指導和幫助。如果想從根本上改變大學里“課堂有教育,學校無教育”令人憂慮的現狀,讓大學教育豐富立體鮮活起來,首先就需要我們的教師從以上三個方面入手,做一個“完整的人”,進而才能從各個方面給學生以引領和指導,為學生指出迷途,問發心靈,訓練思想,導向趣味豐富、人生價值充盈的通衢大道。
三、學術專門化,大學無“文化”
大學教育存在的第三大問題是:學術專門化,大學無“文化”。目前,專業教育日益占據大學教育中的主導地位,大學中出現了過度專業化或職業化的傾向,人文科學受到冷落,導致大學生素質的缺憾和人文精神的滑坡。中國作為文明古國,有著璀璨而傲人的豐富文化遺產,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傳承和發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然而,我們遺憾地看到現在的年輕人離我們的文明日趨疏離,大學的人文氣息正被所謂的“專業化”所掩埋、所吞噬,寶貴的文化遺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長此以往,大學這樣一個民族文化的搖籃和土壤,將成為無本之木,失去其基本的傳播文化的作用,變成生產文憑的加工廠。大學生中沒有讀過孔子的天人哲學、老莊的經典著作、魏晉的高遠玄學、盛唐的豪邁詩文、蘇軾的豪放婉約清曠兼具的詞集或禪宗的妙悟學說……的人居多數,這不得不令人擔憂。如此缺乏中國基礎文化、基本常識和生活經驗的學生有朝一日將居于各行各業的重要崗位,未來實不堪想象。學生的無知,不是學生的失敗,是教育的失敗,是高等教育一再強調“專業化”的流弊。這其實就是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平衡問題。在中國率先提出“通識教育”的清華大學梅貽琦老校長提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10]4中國現代大學的推展者蔡元培先生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日本大學基準協會指出:一般教育不是專業教育的基礎階段,而是本身具有完整性的教育。如果沒有充分寬廣的視野,則可能使專業的深入發展誤入歧途或陷入無用、無意義的境地。一般教育有助于社會上具有各種專業分工的人相互間的溝通理解,并使每個專業的人不至于除了本專業知識,對其他基本社會知識一無所知而陷入生活困境[10]202。專業化教育旨在培養學生將來從事某種職業所需的能力,使學生走向不同的行業和生活,而通識教育意在繼承公共的精神遺產,使人成為有文化,見多識廣的“整全的人”,“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和公民”[11]。在社會對專業訓練需求強勁的今天,更需要通識教育提供一種協調、平衡的力量。故而,我們的大學教育應務必提倡“通學”,把陶冶做人作為其主要目標,把鍛煉體魄,陶冶意志,培養情操,開啟智慧作為首要任務,知識技能的傳授次之[7]230。除了對學生進行文化常識的普及和教育外,我們還應該根據中國的文化特性進行情智教育。在中國,“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中國教育著意生活本身,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12]31。中國人“無論哪一項生活都不喜歡準居于知識”,遇到問題,“總以個人經驗、意見、心思、手腕為對付”[12]29。也正因為此,中國人從來不寫進課本的人情禮儀、處世之道、民俗約定、判斷能力、感悟能力等等,在學生的生活中往往更為重要,這決定了學生是否能夠自如地在社會中生存和與人相處,也決定了他們的幸福指數。作為教師,我們應更多關注學生的情感需要,及時發現學生的困惑,以自身的經歷和經驗引導學生正確認識和看待面臨的矛盾和苦惱。同時,我們還應清楚地看到現代大學生在道德禮儀、社會責任感等方面存在的缺失甚至是錯誤的作為,給予他們正確的反復教育引導。要對學生做好情知兩方面的教育,就要求我們教師首先要遵循中國的道德準則,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廣博的人,一個有趣的人,一個會生活的人。
四、結論
“一國的大學教育,乃是一個國家文教大業之所寄……是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之中心集散點。”[7]199錢穆先生說中國的學問有三大傳統:第一,“人統”,“學者所以學做人也”。一切學問,主要用意在學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個有理想有價值的人。第二,“事統”,以事業為其學問系統之中心,即“學以致用”。第三,“學統”,以學問本身為系統,“為學問而學問”[13]。這何嘗不是我們大學教育之目的所在呢!德國哲人耶士培在《大學理念》一書中強調:大學之使命只在忠誠于真理之探索,大學教育之目的在于模鑄整全的人。耶士培主張在教學與研究之外,大學更應措意于創造性之文化強調[14]。英吉爾大學將大學第一年定為“基礎年”,旨在探討西歐文明之背景、遺產、成就及其問題;美國的博雅教育、通識教育;香港大學由書院提供通識教育等等,這些策略都是可借鑒和學習的。“凡屬變,定是主動的,定是在其內部自身的。”[7]204大學教育要從根本上改變現狀,必先從內部開始,從教育目的的設定出發,讓文化多一些,功利少一些;讓未來多一些,現實少一些;讓理想與興趣多一些,薪資和社會地位少一些,讓學生明白人的最高需求和滿足最終來自于人的精神而絕不是物質。“教育應該教我們頂天立地,我行吾素,寧做裝癡作聾的奇士,勿做糊涂嚴肅的蠢材。”[6]108大學教育應成為完善生命的土壤、空氣和水分,而不是化肥和催熟劑。我們的大學應該始終遵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真理,兼容并蓄,博大豐富,成為優秀民族文化傳承發揚的沃土,為國家培育一代又一代思想獨立、博學敦行、情志高尚的“完整的人”。
[參考文獻]
[1]王輝耀.二戰后美國人才戰略的演化[J/OL].[2015-08-12]
[2]劉寶存.科爾大學理念述評[J].比較教育研究,2002(10):10.
[3]紐曼.大學的理念[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
[4]陳洪捷.德國大學觀及對中國大學的影響[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37.
[5]懷特海.教育的目的[M]∥華東師大出版社,活頁文選,1998:1.
[6]林語堂.論學問與知趣[M]∥林語堂.孔子的幽默.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
[7]錢穆.文化與教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8]竺可楨.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M]∥文化的盛宴.古青山,編.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71.
[9]梁啟超.為學與做人[M]∥文化的盛宴.古青山,編.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1.
[10]陸一.教育與文明:日本通識教育小冊[M].北京:三聯書店,2012.
[11]哈佛委員會.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40.
[12]梁漱溟.讀書與做人[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
[13]錢穆.有關學問之系統[M]∥錢穆,中國學術通論.臺北:臺北學生書局,1977:225-226.
[14]金耀基.大學之理念[M].北京:三聯書店,2008:79.
作者:侯樂旻 單位:太原學院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