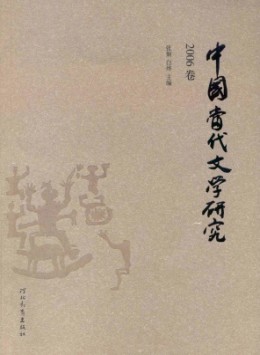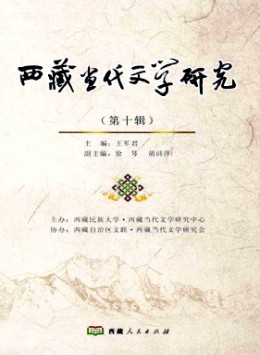當代文學入史問題探索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當代文學入史問題探索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內容摘要:新時期以來的30年,當代文學史寫作進入繁盛期,關于當代文學的入史問題,學術界存在“當代文學不宜入史”、“重寫文學史”等不同聲音,探討當代文學入史問題對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及當代“經典”的塑造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關鍵詞:當代文學入史問題當代文學史寫作
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定義,從時間層面上限定,大多數文學史的編寫一般指的是1949年以來的中國文學,陳思和在《當代文學史教程》前言中,則把當代文學限于1949年后的中國大陸文學。可見,在時間的界定上,當代文學是從1949年以來,發展到社會主義階段后的文學現象,正由于時間仍在延續,學術界對當代文學入史問題存在不同的聲音。
一.關于當代文學是否入史問題的探討
對于“當代文學不宜寫史”而是應該寫述評的觀點,早在上世紀80年代,唐弢等人就已提出。1985年唐弢先生在《文匯報》上發表《當代文學不宜寫史》,他認為歷史是事物發展的過程,現狀只有經過時間的推移才能轉化為穩定的歷史。唐弢先生的這一提法與當下很多評論家、史學家提出的“當代人不宜寫當代史”的說法有著其相同的地方。他們認為,當代文學史應該是留給后人寫的,當代人生活在當下,無法做到“客觀主義”。“這不是因為‘客觀主義’過去遭人忽視,而是因為前朝歷史只能由后朝修,身在前朝是沒法做到‘客觀主義’的。”[1]施蟄存在唐弢之后,也提出了“當代事,不成‘史’”,他認為一切還在發展的政治、社會及個人的行為都沒有成為“史”。當代文學在時間上是開放的,不是說它發展到20世紀末,甚至是21世紀末,就意味它的結束。它在時間上有很大的延展性,如果按照“后朝人寫前朝史”的說法,“當代文學史”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于空缺狀態。唐弢和施蟄存都認為當代文學因為仍然在發展,不適合做文學的發展歷史,應該用“述評”代替“史”。述評,就是敘述并評論,也指一種夾敘夾議的文字,從這個意義上講,述評指的應該是一種文學批評。韋克勒就文學評價這個問題,提出過這樣的觀點:“在文學評價這個問題上,文學史家和批評家沒有甚么不同;他們的真正分野在于一個重點:文學批評家究心于個別作品或者作家,而文學史家要追蹤文學的發展。”[2]述評具有開拓性,不論是對作家作品,還是文學現象的批評,它會由于批評家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變化,這也體現了當代文學“正在發展”的特殊性。持不同意見的吳義勤在否定“當代人不宜寫當代史”的觀點中,提到“拿中國現代文學來說,它的經典化和歷史化是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進程一直是同步進行的。”[3]魯迅在教學期間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略》這些影響后世的文學史著作正是在當下完成的。文學史雖作為“史”,因其史料的無限性,它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文學史寫作角度呈現多元化,它會隨著史料的不斷發掘與更新,也會出現新的角度與切入點,并不是說只有穩定的歷史才能寫成“史”。同理,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同樣可以與發展中的當代文學同步進行,就“文學史”寫作本身而言,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可以是“發展的”。當代文學因其所處的特殊的時間與空間環境,有獨特的運行軌道與風貌,文學史的書寫,可以揭示其獨特發展規律。歷史需要穩定,這是必然的,但歷史的寫作卻不是一元的,固步自封的,當代文學宜不宜入史,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不管是述評還是“入史”,內容、角度和梳理文學發展脈絡的方法更關鍵。
二.對當代文學入史角度的一點看法
1.關于大眾文學與網絡文學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的提出,越來越多學者認為應該把文學史重新整合。既是“重新整合”,應設立相應的標準,現有的當代文學史著作,其寫作范式和切入角度也在變化當中。具有較大影響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洪子誠著),不僅使文學史的寫作范式從集體寫作進入到個人寫作,還將敘述的重心放在了史料的考證上。陳思和的《當代文學史教程》也體現了作者的創新之處,與文化聯系在一起,對作家作品進行評價,提出了“民間意識”、“潛在寫作”,甚至將文學與音樂結合起來。這些變化都說明了,每個時代都有其主導的問題意識,文學具有特定的時代特征,文學史的意義與目的也在于揭示文學發展的規律。從這個意義出發,筆者認為當代文學史寫作,應該注重結合當下,體現文學在時代進程中的意義。90年代以來暴發狂漲的市場利益驅動,出現了除傳統文學之外的消費文學、影視文學,又有20世紀末異軍突起的網絡文學。隨著自媒體的快速發展,寫作者、讀者群體的擴大,大眾文學與網絡文學的出現與發展是當代文學不能忽略的重要文學現象,與傳統文學相比,它們的娛樂功能更突出,在審美功能與藝術性上要稍差,一定程度上,雖良莠不齊,本質上卻是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另一種形式的呈現,它對當下人們生活起著重要的作用。根據丁帆等人的意見(重寫文學史),文學史的寫法應該注重全面性,因此文學史寫作應納入除傳統文學外的其他文學形式。文學史研究的對象既有經典作品,也包含文學現象的研究,在現存的當代文史著作中都少有關于大眾文學和網絡文學的選編,當然,大眾文學和網絡文學在其審美上有著不能忽視的缺點,入史,只能建立一種規范了。
2.對當代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
對當代作家的評價應該用發展的眼光。丁帆的“大文學史觀論”,是要梳理文學發展的內部規律,打通現當代文學。如“不將‘反思文學’與二三十年代的‘問題小說’進行比較,也許就不能看出它與“五四”啟蒙文學的關聯性。”[4]因此,在評價當代作家和作品時,也應該看到他們與前期文學的關聯性。現存的當代史著作中,對八九十年代的作家評價都較為簡單,一方面,當代文學仍然在發展當中,“文學史”較“文學”在時間上應該說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入史相對來說也比較困難。另一方面,對部分作家的評價角度,并非全面。洪子誠的《當代文學史》里,將八九十年代的作家根據其創作的特點進行分類。如按文學的“尋根”、鄉土小說、“先鋒實驗小說”、“新寫實小說”、“女性文學”等等的編排。當代的眾多作家都是進行時的作家,其創作是不斷發展甚至是不斷變化的,并不會因為某部作品的思想內容或者形式帶有某種主義的特點,就是某主義文學。例如,作家閻連科,有評論家將他定義為現實主義作家,也有人認為他是鄉土小說家,從《日光流年》的“倒放”式文本寫法到《風雅頌》里的荒誕,這些都說明了他在寫作上的變化與創新。東北女作家遲子建,在著作中被歸入了“女性文學”中,但遲子建的創作并沒有太大的女性文學的特點,她提供了新的寫作范式,在當代女性主義發展的今天,她倡導的是男女和諧共生,從另一方面說,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越來越多的讀者關注女性文學創作,著作中對“女性作家”與“女性文學”的闡述,又為當代文學史的寫作提供了新的角度。唐弢《關于重寫文學史》認為文學史可以有多種寫法,不應當也不必要定于一尊。文學具有書寫時代的功能,如何用發展的、不斷變化的角度當對代作品和作家進行分析和評論,根據分析和論述呈現文學發展脈絡與規律,呈現時代特征,是文學史寫作關注的重要角度。
三.當代文學史寫作與當代“經典”之關系
當代文學因其時間和空間,所處的內部、外部環境的特殊性,許多人認為“當代無經典”,讓當代文學處于尷尬的位置。涉及何為“經典”的問題,發的《評判與構建》中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到底經典的標準是什么?有評論家認為,每個讀者都可以是“經典”的命名者,對作家作品的閱讀與接受,確實是“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若每個讀者都有一個經典,其規范和標準又從何而來呢?經典的塑性與文學史寫作是否有著相互的影響呢?筆者認為,這是肯定的。讀者作為接受者,除了個人的閱讀經驗以外,教育背景,理解領悟能力的不同,會不同程度地受文學史或文學批評的影響,這時的評論與文學史成了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傳播媒介。因此,文學史的寫作對作家作品經典的塑造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唐弢的《關于重寫文學史》:“只要是真正的文學史,不妨有多種寫法,讀者是多層次的,需要多層次的詳簡不同的文學史,因此可以有多種多樣的寫法。”[5]當前的文學史著作中,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王慶生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等影響較大,回顧現代文學史著作可以看到,大多數的文學史寫作,都會納入“魯、郭、矛、巴、老、曹”的作品,無疑,這些作家在現代文學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與作用,自80年代提出“重寫文學史”以來,有人提出對文學史的寫法應該適當精簡,但是經典的作家作品,是無論如何精簡,也不會將其排除在外的,同樣的,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在作家作品的評價上會對當代經典的塑造有一定的影響。當下越來越多“當代無經典”的聲音,對當代文學史的寫作應該是有一定激勵作用的。文學史的選編,尤其是對作家、作品的選擇和評論上,應該建立一定的標準,書寫文學發展規律及脈絡,體現時代特征,盡可能地對當代文學“經典”進行塑性,讓“當代無經典”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甚至消除這種聲音。
參考文獻
[1]袁曉波.我愿景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03)
[2]陳國球.結構中國文學傳統[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3]吳義勤.我們為什么對同代人如此苛刻?—關于中國當代文學評價問題的一點思考[J].文藝爭鳴,2009(09)
[4]丁帆.關于建構百年文學史的幾點意見和設想[J].文藝評論,2010(1)
[5]唐弢.當代文學不宜寫史[A].孔范今,施戰軍.中國新時期文學史研究資料(上)[C].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235
作者:謝菊 單位:廣西衛生職業技術學院